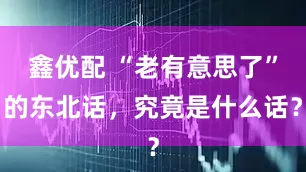
 鑫优配
鑫优配
全文共3205 字 | 阅读需10分钟

“艾玛,这可咋整?”
“这菜老好吃了,嘎嘎下饭!”
“波棱盖儿卡马路牙子上秃噜皮了”
几十年来,自带喜感的东北方言席卷全国,俨然已成为“快乐密码”。有网友调侃:“解释一句东北话,结果要用到更多的东北话。”这看似戏谑的评论背后,却暗藏着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:神奇的东北话,究竟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呢?


▲烟火气十足的东北话。(图片来源:央视新闻)
拨开喜剧滤镜,这些充满生命力的方言词汇,实则是东北地区民族交融的“语言活化石”。
明清时期东北地区的各民族呈现出双向互动特征:既有“自上而下”的政策引导,又有“自下而上”的民间自发迁移;既是朝廷治理的结果,更是百姓在贸易往来中自然形成的文化交流。
深入考察这些方言词汇的源流,我们会发现:东北传统游戏“嘎拉哈”(动物的腿部髌骨)是满、锡伯、鄂温克、达斡尔语“嘎尔出哈”的汉语音译;而形容人固执的“犟眼子”则带有明显的胶辽官话口音特征。这些语言现象不禁让人追问:是怎样的历史机遇,让多元词汇在东北大地相遇,并碰撞出如此精彩的语言火花?
(一)移民热潮下语言的接触与交融
明清之际,辽东地区连年战乱,当地居民纷纷外迁避祸,后来清兵入关更加剧了当地人口稀少的状况。清廷曾发布两次谕令,鼓励汉人进入东北开垦荒地,如顺治十年(1653年)颁布的《辽东招民开垦条例》。
条例宣布开放辽东,奖励官民招揽、应招。在这一优惠政策的激励下鑫优配,“燕鲁穷氓,闻风踵至”,虽规模有限,但也迎来了汉人移民东北的初潮。
后因清初文字狱和科场案牵连,又有大量流人被遣送至东北地区。清代诗人丁介有《出塞诗》云:“南国佳人多塞北,中原名士半辽阳。”可以看出,移民中有不少中原知识分子。他们进入东北地区后以授徒为生,受其影响,东北方言语音呈现出“声调简化,入声调消失以及声韵母简化”的特点。

▲《辽东招民开垦条例》。(图片来源:纪录片《闯关东》截图)
清代中期,山海关内尤其是山东等地人口迅速增多,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,再加上旱灾、涝灾等自然灾害,百姓大批涌入东北谋生。
一时间,“直(直隶)鲁豫晋之人,来者日众”,迎来了向东北移民的高潮。我们所熟知的“闯关东”就是在这一时期发生的。
康熙五十一年(1712年)上谕提到,“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,多至十万余,伊等皆朕黎庶,既到口外种地生理,若不容留,令伊等何往?”
闯关东移民将齐鲁文化、燕赵文化带入东北地区,通过与当地满族、蒙古族等民族通婚,促进了多民族文化交融。
以山东、河北为主的移民带来了幽燕方言,与满语残留词汇结合,如来自山东的方言“客”(音:qiě,意:客人)、“加钢”(故意插嘴说激怒争吵者的话)、“肉头”(犹豫,不干脆)等,深刻影响了东北方言。
随着移民规模扩大,山东、河北等地的官话在交汇融合中逐渐形成东北官话的雏形,其中黑龙江因移民来源混杂,其方言最接近普通话。

▲闯关东的“关”指的是山海关,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境内,素有“天下第一关”之称。(图片来源: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网站)
1858年至1860年间,趁英法联军侵华之机,沙俄胁迫清政府签订《瑷珲条约》与《北京条约》,强占黑龙江以北、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中国领土。此后,日俄为争夺东北权益爆发战争(1904—1905年)。
面对疆土沦陷与战乱威胁,军机大臣徐世昌在《密陈通筹东三省全局折》中提出“充实内力”与“抵制外力”并举的东北振兴策略。在此背景下,清政府推行“移民实边”政策,掀起了新一轮移民边疆热潮。
国内的边疆移民深化了汉语方言和当地民族语言的融合鑫优配,外国人的涌入也对东北方言产生了影响,其中主要以音译形式融入:俄语如“拔蹶子”(走)、“玛达姆”(夫人,妇女);日语如“榻榻米”(铺在床板上的草垫子);朝鲜语如“唧个啷”(争辩,吵嘴)。

▲哈尔滨市中央大街,沿街有多处近百年历史的欧式建筑。始建于1898年,旧称“中国大街”,主要为外国人经营商店的街道,1928年改称中央大街。新华社发(张树 摄)
(二)朝贡之路下的语言交汇“自贸区”
除清代大规模移民带来的语言交融外,一条肇始于更早时期、连接东北边疆与内地的朝贡之路,同样成为多民族语言接触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。
在“厚往薄来”的朝贡政策下,中原王朝对边疆及周边政权往往采取“赏大于贡”的怀柔策略,唐代便有对渤海国使臣“依品赐冠服”的记载。这些身着中原丝绸官服的使者荣归故里时,无形中在东北与中原之间开辟了一条特殊的朝贡之路。
明初因马匹稀缺,朝廷向蒙古、女真诸部大量购马,并推行贡赏制度,吸引北方部落归附贡马。鉴于辽东开原“控临绝徼,翼带镇城,居全辽之上游,为东陲之险塞”的战略地位,明廷于永乐四年(1406年)特设开原马市。

▲明代马市贸易复原图。(图片来源:澎湃网)
开原马市设立后,蒙古、女真、汉等多民族往来贸易频繁,形成了独特的语言混合环境。据辽东档案记载,女真人常因“盐不得吃,布帛不得穿”而依赖马市,这种密切的接触极有可能加速了语言词汇的借用与简化。
明嘉靖年间(1507—1567年),马市已演变为综合性商品交易市场。之前,明廷于永乐七年(1409年)在辽东设安乐州、自在州安置内附女真人,推动满汉杂居。他们在与汉人共同生活中逐渐采用汉语,但仍保留部分本族词汇(如“嘎拉哈”“乌拉草”)及语法结构(如动词“整”“造”),被吸收融入东北方言。
作为朝贡体系下的特殊枢纽,开原马市催生的多边贸易、族群互动与文化互鉴,实质上构建了一个跨民族语言交融的“自贸区”,为语言融合提供了社会土壤。东北方言的多元性和通俗性,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生动体现。
(三)“长在笑点上的话”,
尽显文化活力
东北方言自形成以来便体现出语音、腔调和内涵上幽默而富于感染力的地域特色。有趣的是,许多东北人都坚定地认为自己说的就是普通话。
在语音方面,东北方言呈现出鲜明的特征:一是平翘舌音区分不明显,如“四”(sì)与“十”(shí)均读作平舌音;“支持”(zhī chí)常被读作“zī cī”;二是轻声运用较多,如“玻璃”(bō li)中的“璃”字发音轻而短促;三是儿化音运用广泛,赋予词汇生动活泼的韵味。

▲“沙楞儿”表示快速、麻利、熟练的意思。“沙楞儿滴!”就是要求对方加快行动的速度。(图片来源:辽宁消防微信公众号)
语调方面,东北方言的抑扬顿挫尤为明显。以“你干啥去啊”为例,普通话语调较平稳,东北人说起来,“干啥”会语调上扬,“去啊”则语调下降且拖长音,形成独特的韵律感。这种富有音乐性的语调特征,成为东北方言辨识度的重要标志。
词汇系统更是东北方言的精华所在。大量词汇既幽默又内涵丰富:如“忽悠”不仅有欺骗的意思,更暗含诙谐意味的处事态度;“嘚瑟”有炫耀、张狂之意,但在东北方言中,有时也可用于朋友、亲人之间的亲昵调侃。这些词汇往往更具情感张力和表现力。

▲“五脊六兽”,原指屋顶上的脊兽装饰,在东北话里被巧妙转化,用“神兽蹲在屋顶无所事事”的意象,来形容人闲得发慌、心烦意乱或行为滑稽的状态。(图片来源:新浪《乡村爱情》官微)
东北方言的幽默特质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结晶,体现了东北人的生活方式。从清代移民潮带来的方言融合,到少数民族语言的渗透影响,再到当代网络文化的推波助澜,东北话始终保持着开放包容的姿态,展现着东北人“敞亮”的生活态度。这种“长在笑点上的语言”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,也为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增添了活力。
【作者简介:王思莹,大连民族大学2024级民族学硕士研究生;陈煌旭,大连民族大学2023级民族学硕士研究生;戴嘉艳,大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(学院)副教授】

(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本号立场)

天宇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


